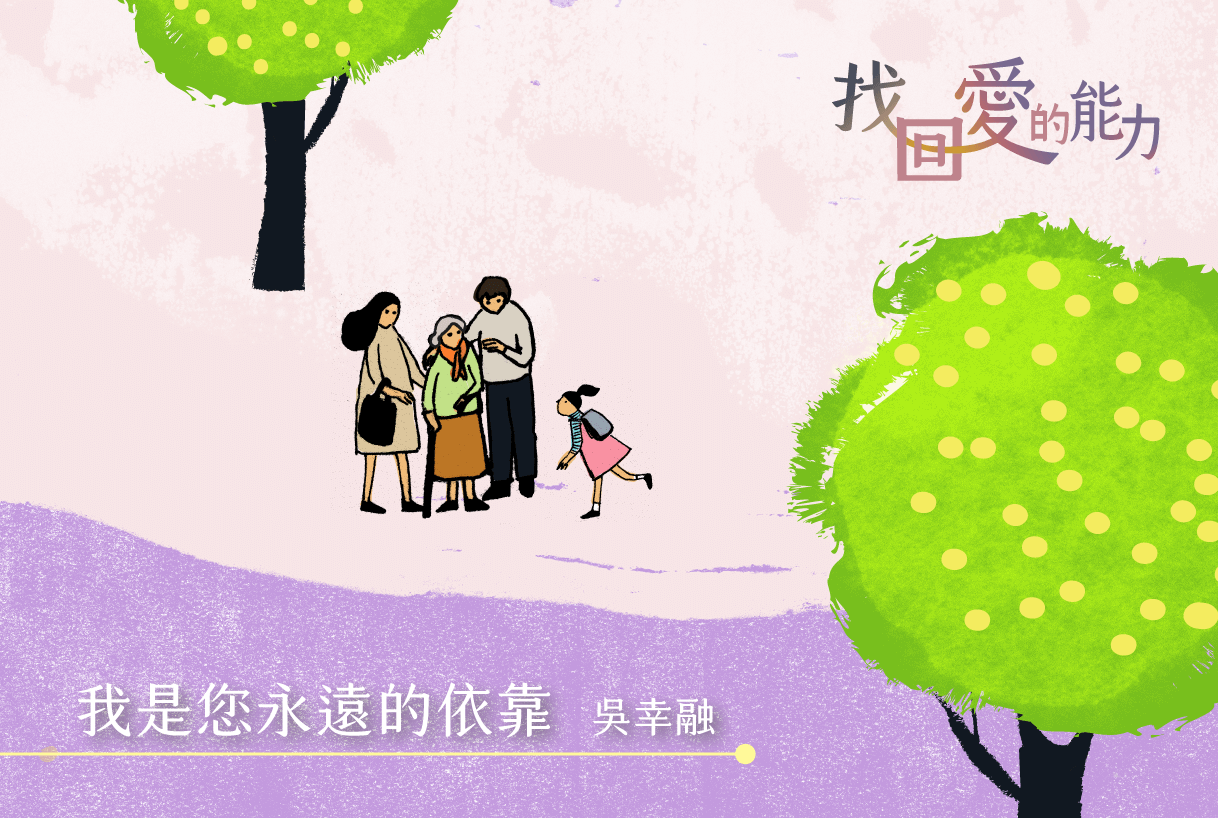「爸爸」兩個字,對我來說是陌生又遙遠的詞彙。從小沒了爸爸的我,每年父親節總顯得比平常還要沉默,只因我不曉得在這個為了父親慶祝的節日,要為誰慶祝?為了什麼慶祝?
對爸爸的記憶停留在六歲以前,住在小小公寓的我總喜歡央求他帶我和哥哥去動物園,然而去了,又因為動物園的場地過於寬廣而腳痠,總會累到生氣。那時候,爸爸會將我放到肩膀上,至今,我依舊記得他因消瘦而突出的肩胛骨,以及他生氣又無奈的嘆息。
後來爸爸走了,年幼的我還不了解什麼是「再也見不到他」,只知道為了生活,媽媽帶我回到娘家,不再蝸居在台北,讓我擁有一整片可以奔馳的田地。直到長大進入青春期,我的人生初次面臨遲來的尷尬與彆扭。我開始閉口不談爸爸,每年的父親節總裝作若無其事,以為偽裝自己就能假裝一切安好。
以前的我常常幻想有一天步入禮堂,我的爸爸會牽起我的手,將我交付給另一個男人,然後叮囑他好好照顧我。可我終於明白,幻想之所以是幻想,是因為它不會實現。

二十幾年以來,我曾因為自己沒有爸爸感到難過,但重新梳理我的日常,卻會發現比起那偶爾的傷感,我總是笑得開心,或許稱不上陽光,至少能形容是個開朗的女孩。
而這一切都是因為我的媽媽和哥哥。

媽媽很嚴厲,卻也是世上最溫柔的女性,沒了丈夫,她選擇一個人扛起一個家,原本打扮漂亮的她不再裝扮自己,在溫度灼熱的麻油工廠一天一天的工作,麻油香取代了她身上縈繞的香水味。然而工作的沉重沒讓她疏於管教我們,她是慈母,卻也扮演了嚴父的腳色。在我做錯事的時候,她拿衣架打我,不因為我哭啼而心軟,堅持要我認知到自己為何被打,希望我不要走偏,然而夜晚降臨,在我哭到睡著後,她也會拿著藥擦在每一個紅痕上,心疼地為我撫平傷痛。
哥哥則取代了父親帶著我玩的形象,大我一歲的他很溫和,總配合我玩扮家家酒、洋娃娃,卻也帶我去放風箏、玩遊戲王卡。年紀大一點,他拿自己的零用錢買餅乾給我吃。等到我成了一個叛逆的青春期女孩,開始偶爾和媽媽頂嘴,哥哥總會居中協調、緩和,私底下勸戒我。

爸爸留下的空缺看似無可彌補,但我卻擁有媽媽和哥哥雙倍的愛,讓我成長的過程從沒有機會感受到孤獨。雖然,我還是很想念爸爸,偶爾也想過,如果爸爸在身邊該有多好,我卻也知道,有媽媽和哥哥的我是何其幸運。
「父親」依舊是個遙遠而陌生的詞彙,只是我卻想通了,我的母親就是我的爸爸,我的哥哥,則補足了爸爸帶來的缺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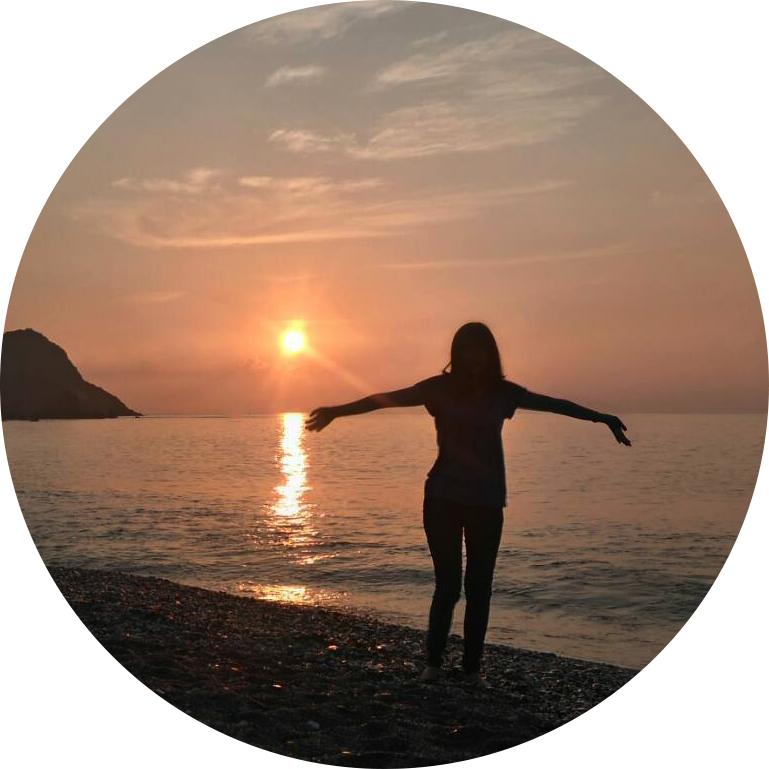
專欄作者 Sunny
興趣廣泛,但最割捨不下的還是閱讀,從散文、小說到漫畫都是涉略的範圍。總在腦內上演很多小劇場,任思緒奔騰跳躍,然後化為片段的字句用筆尖留下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