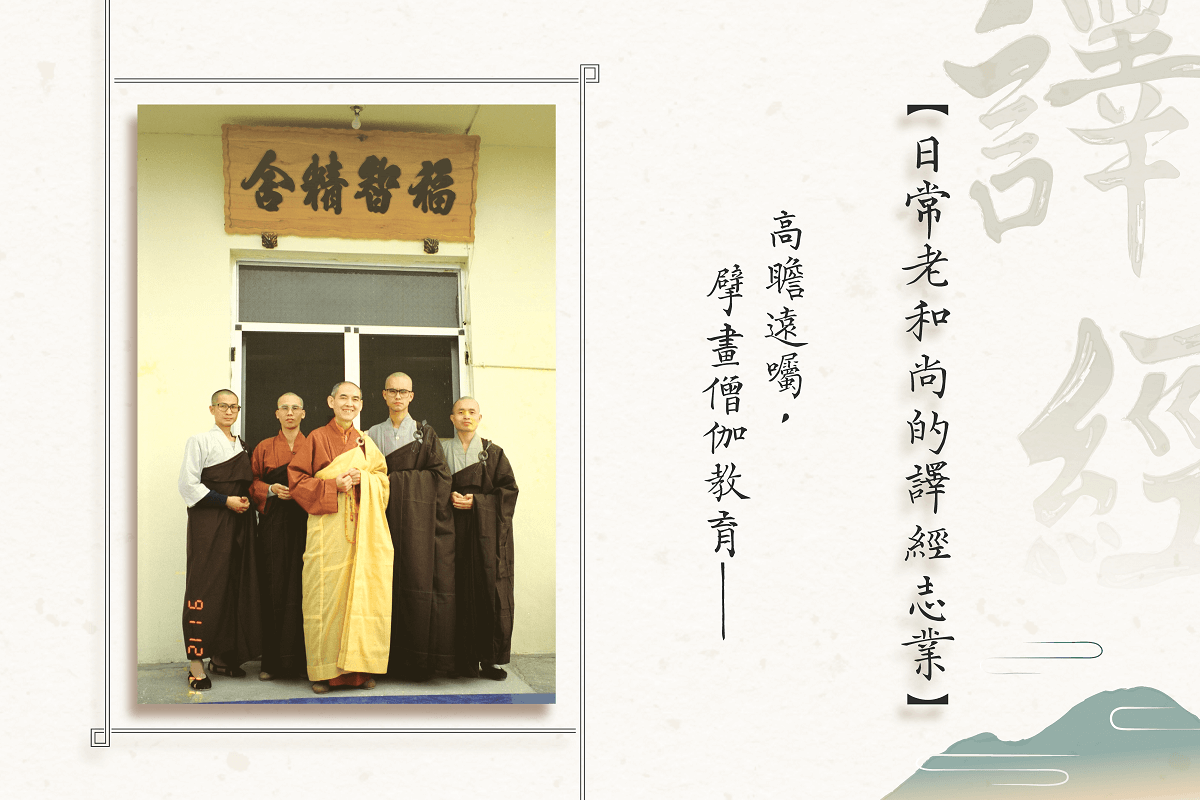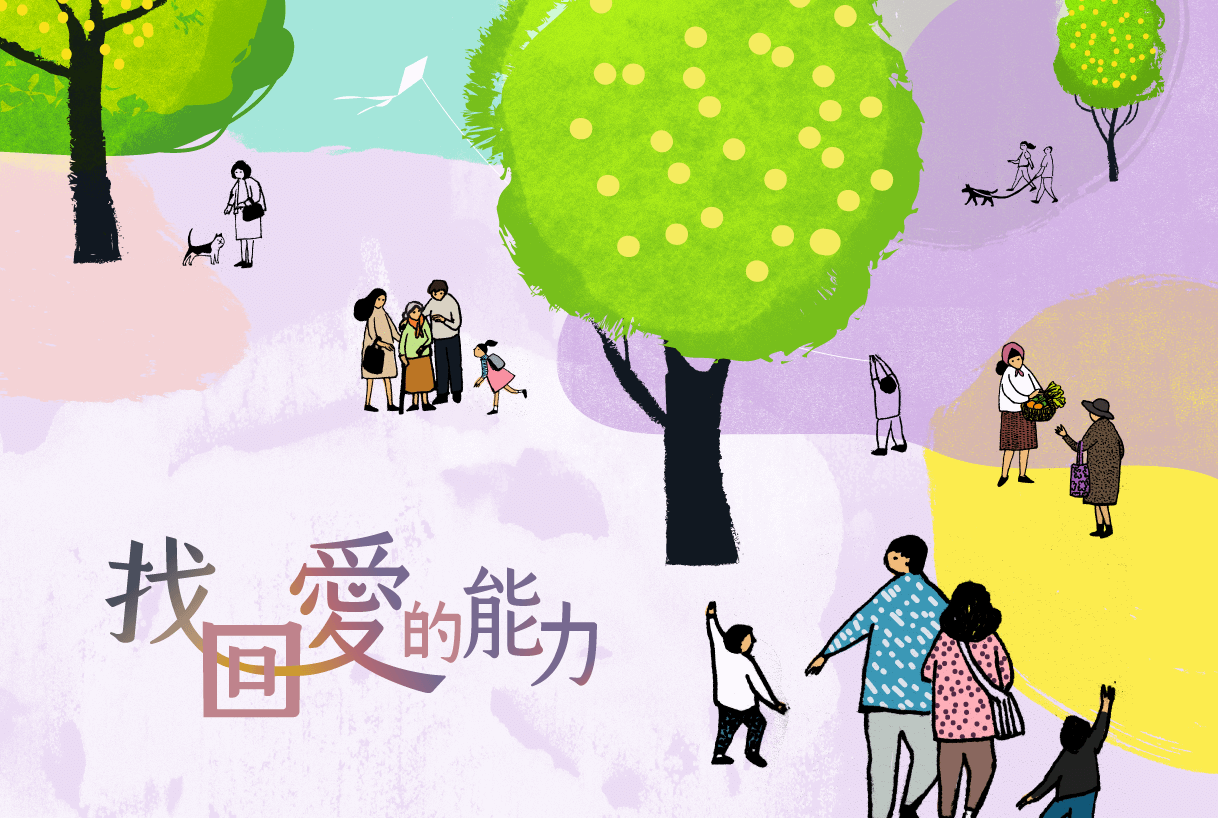有一種樹,或許你不知道它的名字,但你一定見過它;有一種樹在久遠的周朝「詩經」裡就有記載;有一種樹,跟著人類的步伐,從台灣出發,直到南美的復活節島落腳,這個看似平凡卻很不平凡的樹種就是「構樹」。
構樹一身是寶,嫩芽嫩葉是鹿的最愛,有「鹿仔樹」之稱,又名「楮樹」「楮桑」。因樹皮多纖維,漢朝以來就用來造紙,宋元之後,更是紙鈔銀券的主要原料,因此「楮先生」「楮墨」、「楮」就成為文稿、錢幣的代稱了。
昔無楮先生,云自蔡倫始。假令行竹簡,禿野未供使。 ——(宋 孔平仲)
若人富天巧,春色入毫楮。 ——(宋 蘇軾)
物貴皆由楮幣輕,近聞五嶺亦通行。 ——(宋 劉克莊)
一千新楮券,三百舊銅錢。 ——(宋 華岳)
蔡倫造紙改變了以竹簡書寫的歷史,銀券紙鈔更開創了新的幣制,構樹在人類文明史上扮演了關鍵的角色,「紙木」「鈔票樹」之名,實非浪得。

構樹不僅可用,更可穿上身,由捶打、分離構樹樹皮,再延展、風乾、縫製的「樹皮衣」,是「南島語系民族」共有的生活技藝。曾有人類學、生物學等學者大膽假設:「南島語系民族出台灣說」,經由台灣學者與智利專家小心求證,運用繁複生物基因檢測技術,證明智利復活節島太平洋構樹的原鄉即是台灣。數千年前,先民從台灣出發,沿著島嶼一路遷徙直至太平洋彼岸的南美洲,所攜帶的構樹種子也在異鄉落地生根,構樹樹皮所製作的「樹皮衣」就是串起這遷移軌跡的樞紐,構樹在人類生活中的影響再添一樁。
學者專家們的研究或許不容易理解,但主導以上研究的臺大森林環境暨資源系鍾國芳教授的一段話我們一定聽得懂:「從台大校門口到森林學系這段路,你可能經過了200棵構樹而未察覺」,構樹隨處皆有可見一斑。構樹葉子有多種形狀:掌狀、心形、卵形等,較易混淆 ,然花果則極易分辨:「公花母花不同叢,公花長長親像蟲,母花圓圓像金含(小時候吃的圓圓的糖球),花開給風作媒人」,構樹雌雄不同株,四五月開花時,公花像掛在樹上的毛毛蟲,而雌花則朵朵圓潤如糖球,風媒授粉後雌花結成一顆顆橙紅的聚合果,像極了掛在樹上的小鈴噹,所以又有「噹噹樹」的俏皮稱號。

每年七到九月,不妨趁著構樹結果期,循著那橙紅渾圓的果實尋訪構樹,它在街角公園、路邊雜樹叢,甚至是荒地一隅都有可能現身。或乾脆直衝臺大校園,去探訪那傳說中的兩百棵構樹。只要找著那橙紅渾圓的果實,構樹公株應該就在不遠處,何妨拾起新鮮落果一嚐,享受那酸酸甜甜的特殊風味,如在樹下流連夠久,當可與白頭翁、綠繡眼、麻雀、斑鳩等相遇,因為甜蜜多汁的構樹漿果也是鳥族的最愛,一趟盛夏的構樹之旅,不僅可親見構樹身影,更可體驗「好鳥枝頭亦朋友,落花落果皆文章」的悠然意境,何樂不行呢?

📘國學私房課,點擊看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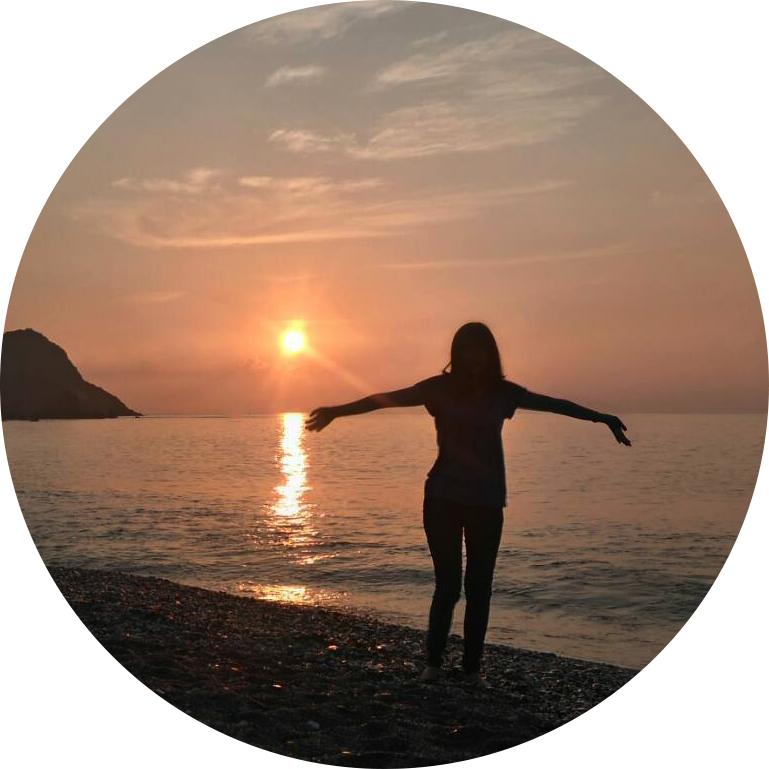
專欄作者 Sunny
興趣廣泛,但最割捨不下的還是閱讀,從散文、小說到漫畫都是涉略的範圍。總在腦內上演很多小劇場,任思緒奔騰跳躍,然後化為片段的字句用筆尖留下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