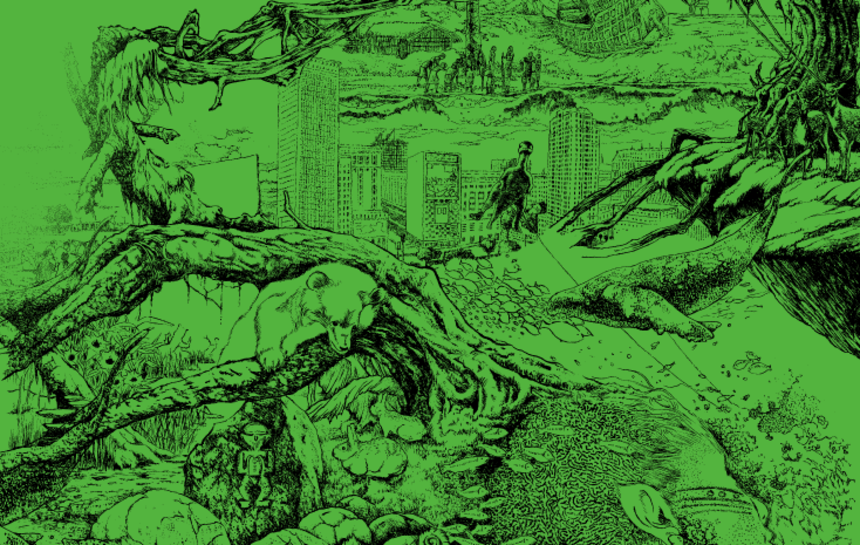2010年時,黑潮集結臺灣五個長期關心海廢議題的非營利組織,共組「台灣清淨海洋行動聯盟」,並著手簡化ICC版本的表格,製作出「臺灣ICC淨灘監測紀錄表」,從原本的八十多項直接減少到十九項臺灣最常見的海洋廢棄物來做監測………
「我就是來海邊撿垃圾啊,到底為什麼還要再跟我收錢?我還要付錢來撿垃圾,那我自己來撿就好啦!」
線上訪談那頭的男子突然化身為氣憤的民眾,字字鏗鏘有力,但話鋒一轉,他語氣轉為平和,「2005年左右的時候,臺灣還沒有太多人關注海洋廢棄物的議題,民眾不理解辦活動須要辦保險,那時候我們推的很辛苦。」
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執行長林東良回憶起多年的往事,一人分飾兩角,生動地說明黑潮早年推動關注海廢議題的困難,「來撿垃圾這件事情就很辛苦,」林東良說到被民眾質疑撿垃圾還要收錢是假公益,感到無奈,「我們一開始在推的時候真的是沒有太多人理解。」而成立於1998年的黑潮如今以保育鯨豚聞名,但鮮少人知的是,他們也是臺灣最早關注海廢議題的組織。

淨灘不只是撿垃圾
「2013、2014年,開始有網紅用複合方式辦淨灘,像是台客劇場和RE-THINK的電音淨灘,就吸引了一千到三千多人一起去海邊淨灘,一起開Party。」但一場場動輒聚集千人的海灘大型活動,事實上也是在黑潮推動淨灘十年後才出現的現象,曾經黑潮辦的活動就只來幾個人,且對於議題理解有限。林東良說起這段臺灣淨灘的演變史,並未沉溺於過往的不順,而是將焦點放在現在急需克服的難題,「ICC淨灘推到現在,我們的政府部門也才開始意識到,ICC的方法跟一般淨灘是有差異的,」他停頓了一下,語氣慎重地說明關鍵的差異:一般的淨灘是撿垃圾、秤重、拍照,紀念一起做了公益的事情,「但是ICC方法最主要的重點是,讓記錄的數據幫助我們回到源頭管理。」
「源頭是什麼?就是政策的源頭。」林東良細心解釋,國際淨灘行動(International Coastal Cleanup, 簡稱 ICC)方法的目的,「不只是要把海灘清乾淨而已,而是要做長期監測。」在民主社會裡,不論是對民眾呼籲進而形成民意,或是推動公部門制定政策,都需要有數據的支持,才能有效推行。那麼,黑潮從保育鯨豚到關注海廢議題的源頭又是什麼?
那是黑潮成立後二年,也就是2000年時,當時林東良尚未加入黑潮,但這段一切起源的故事卻是每個黑潮人,也是臺灣關注海廢的起點。
黑潮推動臺灣ICC淨灘的開端與變革
1980年代,四面環海的臺灣,對於海洋廢棄物漂流全世界,嚴重危害海洋環境及海洋生物的國際討論,卻知之甚少。但開始得晚,總比沒開始來得好。2000年,夏威夷舉辦「海上漂流廢棄物國際研討會」,黑潮派員參加,在研討會上一次大補帖更新國際動向,除了了解各國對海廢的討論,學到ICC淨灘的方法,也成為黑潮日後在臺灣推動淨灘的有利基礎。
2010年時,黑潮集結臺灣五個長期關心海廢議題的非營利組織,共組「台灣清淨海洋行動聯盟」,並著手簡化ICC版本的表格,製作出「臺灣ICC淨灘監測紀錄表」,從原本的八十多項直接減少到十九項臺灣最常見的海洋廢棄物來做監測。「所以現在辦淨灘就變得比較簡單,也比較容易上手。」林東良過去常聽見民眾反應表格有八十幾項,要登記都要找很久,但隨著簡化到十九項,又是與生活有關的項目,大幅提升登記意願。
當來訪者問起臺灣很常見物品,但卻沒有被列入紀錄表的項目及其篩選的標準為何時?林東良面對提問者的疑惑,用故事清楚舉例,說明追蹤數據與紀錄管理的目的,「我們超級容易在海邊撿到鞋子的,但它很難回到源頭管理,因為每個人都穿,所以你不知道最後你要管理的對象是誰。」依照同樣的邏輯,林東良也以秀姑巒溪泛舟為例,「溪口會看得到特別多的水瓢,我也是查了影片才知道,原來泛舟時會帶水瓢,但水瓢如果不小心流走,就會成為廢棄物。」像這類沒出現在紀錄表上的特殊項目,就必須回到在地追溯原因,因此目前表格上還是以塑膠製品、個人衛生等民生垃圾為主。

「紀錄是為了能夠回到源頭,透過政策面來改變,最能發揮影響力。」林東良提到,2018年開始塑膠袋隨袋徵收費用後,統計數字下降的改變,「2019年的吸管政策推出時,引起很多人不滿,」原本以為限制吸管使用的政策推動後數字會掉下來,但無奈遇到疫情,吸管目前還是排行第三、四名。但林東良仍對ICC方法溯源,來推動政策的功效表示信心,「以吸管來說,其實有越來越多的店家會選擇用環保材質。」他強調ICC的方法是可以給政府建議,讓政府制定減少廢棄物政策時,可以知道要從哪一個項目著手。
「實行自帶環保杯折五塊後,身邊很多朋友真的因此比較有動力。」林東良表示,雖然塑膠垃圾在數據上仍然居高不下,但是改變並非在朝夕之間,這種政策需要看長期,唯有持續不懈,才能看到成效。
變形的海洋廢棄物
推動ICC淨灘行動近25年的黑潮,對臺灣的海洋廢棄物型態的轉變累積深厚的數據基礎。「我們會建議大家到海邊時,不要打赤腳。」林東良說到近幾年來海灘上出現的危險物品,語重心長地指出,「現在不只是塑膠製品,還出現玻璃與金屬,像魚鉤這種銳利的物品,人若踩到就會受傷。」根據黑潮的統計,臺灣各地從事漁業活動的海岸,出現不少的玻璃罐,如花蓮溪出海口,到了秋冬季捕鰻的季節,漁民因天冷需要酒暖身,卻往往將酒瓶留在原地,變成海邊的垃圾。林東良補充,「特別是像保力達、威士比這一種,因為屬於藥酒,不能夠用一般玻璃回收,很多漁民就沒有意願做。」除此之外,林東良也發現到,天冷時民眾到海邊會生火,把玻璃罐頭丟進去一起加熱,破碎的罐頭碎片讓海灘變得危險,雖然看似隨手便利之舉,卻可能造成遊客與環境的危機。
在一般大眾的經驗裡,隨意棄置民生垃圾會危害海洋是可以連結的,但談到農業廢棄物也會危及海洋生態,就需要花點心力推廣。林東良說,「近期我們在臺灣很多河床地,發現很多黑色塑膠布,」從關注漁業廢棄物到農業廢棄物,都需要花心力仔細找到源頭,「溯源就會發現如種西瓜等農作物,其收成後若農民沒有特別移除蓋布,颱風季節到來,水一漲,就被沖到下游。」而類似的延伸題,正持續地擴張中,考驗黑潮與其聯盟的應變能力。

跨界合作,黑潮推出全臺第一本漁業廢棄物圖鑑
「我們統計的漁網、網針、浮球、浮具,雖然最後重量很重,可是數量不會很多,導致它們被關注的程度沒有那麼高。」林東良將焦點再次擺回近年海洋廢棄物中,急需被重視的一環:漁業廢棄物。然而,漁業是專精的產業,民眾了解甚少,更遑論因漁業產生的廢棄物。黑潮意識到認識漁業的門檻過高,善用ICC紀錄表的特長,標誌出常見的漁業廢棄物,並與澄洋環境顧問合作,共同產製全臺第一本「海岸漁業廢棄物圖鑑」(以下簡稱漁廢圖鑑)。
林東良指出,「民生垃圾中,我們可以很輕易分辨寶特瓶、利樂包,但漁業的用具有其專業度也較罕為一般人所知,但透過圖鑑,產業生產的海廢也能被分類標記。」他以常被忽略的浮球網為例,浮球網是流刺網上的物件,以往大家只關注危險的流刺網,但浮具往往因缺乏溝通、教育訓練或管理而被大量留在海上。ICC方法最重要的宗旨便是回到源頭管理,影響政策,這是林東良與黑潮夥伴們最在茲念茲的事情,「當有了追蹤與記錄,就有機會可以清楚地告訴漁管機關,他們可以怎麼行動,如何設計政策。」
「現在比較大的漁港都已經開始在推廢棄漁具的暫存區,鼓勵漁民不要將破敗的設備直接丟棄於海上與海灘,漁具管理也已經有用『實名制』來回溯使用者,做好源頭管理。」林東良欣慰地說,至於大眾常因為對ICC表格陌生、怯步、無意願理解的心態,他則認為重點還是努力溝通,不論是對製造廢棄物的漁民、來撿垃圾的民眾,甚至是制定政策的機關,都不要放棄。

守護海洋的一個最簡單的行動——從海邊走走開始
「如果我沒有認識到海的話,我可能會不斷換職務。」講起ICC方法時十分理性的林東良,被問及加入黑潮最大的改變,他的語氣轉為感性,直言即便未來某一天卸下職務離開黑潮,他仍然能不斷向海學習,不管換哪個職位,還是會跟海有關。海洋的種子深植在林東良的身體裡,他也觀察到現今校園推廣海洋環境教育時,大多停留在知識的傳輸,少了實際經驗產生連結,而這是推廣時最常見,也最容易被忽略的問題。然而,知識與行動間的斷差有多明顯呢?林東良說,「學生可以很清楚講出哪些物品會危害海洋,但桌上還是擺著用塑膠袋裝著的早餐。」他無意批判,語氣中更多的是對校園教育端未來的期盼。
「我不會覺得學校要每一次活動就是都辦很大、很好,但是確實需要持續去做,因為當你繼續去做,才能跟學校建立保持連結。」林東良也從年輕學子身上看見對海洋態度的轉變,「我們可以感受到現在的年輕人普遍來講對於海的接受度是越來越高,不像我這一輩或者是我的上一輩,對於海都會多少有一點恐懼。」他期許管理政策能重建一個新的海洋文化,未來黑潮推廣活動努力的方向,將更著重於寓教於樂,如結合書籍、繪本等出版。
「有沒有一個最簡單的行動,讓我們可以為海做一些事情呢?」林東良面對來訪者最後的提問,真誠地流露他對海洋的愛與自信,「你只要願意去海邊走走就好了,只要找一個最近的海邊、去那邊看看,聽海的聲音都好。」

👉特別企劃【擁抱島嶼,點亮海洋】完整閱讀